冯书怡 | 思想实验的逻辑结构:以盖梯尔案例为例
点击次数: 更新时间:2024-04-08
【摘 要】思想实验是传统“扶手椅”哲学的重要工具。但许多思想实验处于争议之中,这引发了实验哲学家对“扶手椅”哲学的猛烈攻击。为了解释思想实验的争议根源以及捍卫思想实验作为哲学工具的合法地位,一个工作思路是以澄清思想实验的内在逻辑结构为起点。为此,需要重构盖梯尔案例的逻辑结构。三种传统的重构方案——严格蕴涵解读方案、反事实条件句解读方案和可能性陈述解读方案值得审视,以莫格伦的可能性陈述解读方案为基础,借助公认的“认知运气与知识不相容”预设,可以提供一个改进的解读方案。澄清思想实验的逻辑结构或有助于解释思想实验的争议根源,有助于抵制对实验哲学的攻击。
【关健词】思想实验的逻辑结构;盖梯尔案例;实验哲学;可能性陈述;认知运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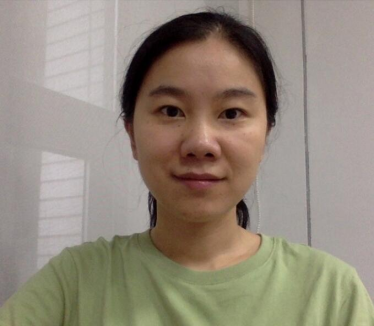
作者简介:冯书怡,suncitygroup太阳新城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模态知识论,聚焦于经验论和理性论,也关注反事实理论。
文章来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50(01)
一、导 言
思想实验是哲学家们评估哲学理论是否可靠的重要手段。如果我们发现一个思想实验传递的哲学直觉和待评估的哲学理论(即靶子理论)相冲突,那么我们往往会质疑待评估的哲学理论。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该理论存在反例,因而站不住脚。以下是两个经典的例子。
例1:盖梯尔案例(the Gettier case)[1]
靶子理论:知识定义的JTB理论。该理论认为:认知主体s知道p, 当且仅当s相信p, s有关于p的辩护证据,并且p为真。
盖梯尔思想实验:假设史密斯相信他办公室的同事琼斯拥有福特车。他拥有这个信念是因为他之前见过琼斯开福特车。从这个信念出发,他进而相信:办公室里有人拥有福特车。事实上,他办公室里确实有人有福特车,但这个人不是琼斯,而是布朗。琼斯的车早就被偷了,他开的那辆福特车是租的。
结论:“办公室里有人拥有福特车”是史密斯的一个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但不是他的知识。因此,知识定义的JTB理论不成立。
例2:僵尸案例(the zombie case)[2]
靶子理论:最小物理主义。该理论认为:必然地,如果现实世界中的所有微观物理属性被固定住,那么现实世界中的所有心灵属性也被固定住。
僵尸思想实验:假设我们把现实世界物理复制一遍。也就是说,复制出来的新世界中,所有的微观物理事实都和现实世界相同,但新世界有僵尸这样的生物,它们的所有物理属性都和现实世界的人相同。它们的疼痛表现和疼痛功能也和现实世界中的人相同。比如,它们被针扎时,也会大喊一声“好疼”,也会缩手,也会尽量避免碰到尖锐的物体以免受伤,但它们体会不到疼痛的感受。
结论:即便世界中所有微观物理属性被固定住,还是有可能存在某些心灵属性,比如疼痛的感受,没有被固定住。因此,最小物理主义不成立。
哲学讨论中用思想实验为工具反驳靶子理论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中文屋思想实验被用以驳斥强人工智能理论:语法并不是产生语义的充分条件,因此,人的心灵不等同于计算机[3]。电车思想实验被用以驳斥功利主义:我们不认为把桥上无辜的胖子推下去挡电车以拯救绑在铁轨上五个人的性命是道德行为,因此,道德行为并不等同于使得福利最大化的行为[4]。孪生地球思想实验被用来驳斥语义内部论:地球人和孪生地球人在使用“水”这个词时,虽然他们大脑的内部状态是一样的,但他们说的不是同一个意思。地球人说的是H2O,而孪生地球人说的是XYZ,所以,语言的意义并不完全由大脑内部状态决定[5]。
虽然上文列举的都是常见的思想实验,但它们的接受度,或者说争议度,并不是相同的。学界普遍认为,盖梯尔案例是成功的:它成功挑战了传统的关于知识的定义——知识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但不少哲学家认为僵尸案例不能击败其对应的靶子理论[6]。也许正是许多思想实验处于争议之中,近十年来,利用思想实验(以及哲学直觉、概念分析)等先天工具进行哲学探讨的方式,即所谓的“扶手椅”哲学,遭到了实验哲学家们的广泛质疑。再如,马克里(Edouard Machery)指出,调查问卷显示思想实验有很多不良特征。比如,对同一个思想实验进行具体程度不同的描述,竟然会导致人们对思想实验蕴涵怎样的结论作出不同的判断。然而,对思想实验进行怎样的描述和哲学问题本身是无关的。所以,马克里认为,既然人们对思想实验的判断总是受到与哲学问题无关的因素影响,这说明思想实验这种先天工具本身就不值得信赖,应当彻底被抛弃[7]。
为了回应实验哲学家的批评、捍卫思想实验作为哲学工具的合法地位,一个尝试性的工作思路是以澄清思想实验的内在逻辑结构为起点。因为即便实验哲学的调查结果是正确的,人们对思想实验的判断确实容易被与哲学无关的因素影响,但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这个影响的来源可能并不是因为思想实验这个哲学工具本身造成的,而是由语言层面的因素造成的。同一个故事,采用不同的讲述方式,人们对故事的理解和对主角是非善恶的判断很可能完全不同,但这种不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受到了自然语言的干扰,而并非人们不具备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如果我们对思想实验的逻辑结构作出澄清,那么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由自然语言造成的干扰[8]。
但如前文所述,哲学各领域的思想实验汗牛充栋,接受度各不相同。那么,我们应该从哪一个思想实验入手呢?在这个问题上,学者们采取了“抓典型”的策略:我们先挑选一个公认为成功的(也就是接受度最高的)思想实验,以澄清这个思想实验的逻辑结构为出发点。只有先做到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完成如下两项工作:其一,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个最成功的思想实验的逻辑结构揭示出来,并从中分析出成功的思想实验需要满足哪些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以此为标准评判其他的思想实验是否(不)成功以及因何而(不)成功,那么,“某些思想实验更可信、某些思想实验争议更大”就不再是一个得不到解释的事实;其二,我们或许能基于第一项工作,尝试抵制实验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攻击:就算人们在使用思想实验这种先天工具时常常得不到稳定的判断,但这种不稳定性是由描述思想实验的自然语言造成的,而不是思想实验这个哲学工具本身造成的。
在所有的思想实验里,盖梯尔案例被公认为是成功的思想实验。所以一般来说,学者们对思想实验的逻辑结构的澄清工作几乎都从盖梯尔案例开始。这也是本文要探索的问题:盖梯尔案例的逻辑结构是怎样的?下文将聚焦于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许多学者已经对这个问题提供了尝试性回答,提出了不同的关于盖梯尔案例的解读方案(但从学界已有的讨论来看,目前已有的答案都不令人满意)。笔者的工作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在对这个问题提供自己的答案之前,笔者必须先展现前序学者的已有回答,并指出他们的缺陷,这样才有可能说清楚为何自己的解决方案比他们更优。
二、 盖梯尔案例的逻辑结构:三种代表性解读方案
首先,我们澄清哲学家们用思想实验攻击靶子理论的思路。“待评估的假说或理论宣称或蕴涵一个模态陈述(通常来说,要么是一个必然性的双条件句,要么是单方向的蕴涵句)”[9]:必然地,如果R,那么S。比如,知识定义的JTB理论(以及其他大多数用“R当且仅当S”来表达核心观点的理论)蕴涵了一个必然陈述:必然地,如果命题p是某个认知主体s的知识,那么p是s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最小物理主义的立场则宣称了一个必然性陈述:必然地,如果现实世界的所有微观物理事实如何如何,那么现实世界的所有心灵事实就如何如何。所以,如果要击败一个靶子理论,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可能性陈述:可能地,R且⇁S。而且我们必须给出理由证明这个可能性陈述是得到辩护的。思想实验就承担了为这个可能性陈述提供辩护的角色。
通俗地说,任何一个思想实验实际上都暗藏了一个结论为“可能地,R且⇁S”的论证。这个暗藏的论证就是这个思想实验的逻辑结构。澄清一个思想实验的逻辑结构,就是把它暗藏的论证重构出来,尽量使它成为一个可靠的论证[10],而且这个重构确实能表达思想实验真正想表达的内容(换句话说,这个重构必须让我们觉得它能完美贴合思想实验传递的信息)。接下来,我们以盖梯尔案例为例,详细考察它的逻辑结构。为了简化行文以及更好地凸显论证结构,我们需要一定的符号语言作为辅助。
K(x, p):x知道p。
JTB(x, p):p是x的得到辩护的真信念。
GC(x, p):x和p处于盖梯尔场景中的关系。[11]
盖梯尔案例攻击的对象是知识定义的JTB理论,或者说,JTB理论所蕴涵的必然性陈述:
∀x∀p(JTB(x, p)=K(x, p))[12]
所以,盖梯尔案例的逻辑结构必须是一个以如下陈述为结论的论证:
◇∃x∃p(JTB(x, p)&⇁K(x, p))[13]
那么,盖梯尔案例暗藏的论证的前提是怎样的呢?以下是常见的三种解读方案。
(一)严格蕴涵解读方案
严格蕴涵解读方案认为盖梯尔案例应被构造为如下论证:
前提1:◇∃x∃pGC(x, p)
前提2:□∀x∀p(GC(x, p)⊃(JTB(x, p)&⇁K(x, p))
结论:◇∃x∃p(JTB(x, p)&⇁K(x, p))[14]
前提1毋庸置疑是令人信服的:显然地,可能有一个认知主体——如“史密斯”,和一个命题——如“办公室里有人拥有福特车”处于盖梯尔场景中的关系。
但学界普遍对前提2不满意。学者们对前提2的不满主要有如下两点。
第一,学界公认前提2为假。
此外,在“为何前提2为假”这个问题上,学界也有一致意见[15]。首先,任何一个思想实验的描述在细节方面都是有缺失的。比如说,盖梯尔案例中就不会提及几位主角穿怎样的衣服,有怎样的兴趣爱好,等等。所以,填充更多细节,认知主体“史密斯”和命题“办公室里有人拥有福特车”仍然可以处于盖梯尔场景中的关系,即填充更多细节仍然可以保证前提2前件为真。其次,前提2是一个严格蕴涵句。严格蕴涵句遵循“增强前件原则(the Principle Strengthening the Antecedent)”:对于任何命题p, q,r, 如果p严格蕴涵q, 那么p和r的合取也严格蕴涵q。所以,假如前提2为真,那么无论我们怎样填充盖梯尔思想实验的细节,前提2都必须为真[16]。但事实并非这样,因为我们很容易找到前提2的反例。比如,莫格伦(Anna-Sara Malmgren)已经指出,我们可以按如下方式填充盖梯尔案例的细节:“设想史密斯有理由相信自己容易产生幻觉——以为别人开着福特车上班;而且他也有理由相信自己总是记错别人以前开什么车。”[17]在填充这个细节之后,前提2的前件仍然为真,但后件为假:“办公室里有人拥有福特车”这个信念既没有得到辩护,也不是“史密斯”的知识。所以,填充更多细节很容易使得前提2为假。
第二,学界公认前提2和盖梯尔案例表达的内容并不相符。
更具体地说:前提2比盖梯尔案例实际想传递的意思强太多。这一点同样是莫格伦指出的:严格蕴涵解读太强了,所以我们非常容易就找到了前提2的反例。但我们在阅读盖梯尔案例讲述的故事时,我们的观感却不是这样:至少乍看上去,盖梯尔案例传递的信息是可信的,不太容易遭遇反例[18]。这说明,前提2表达并不是盖梯尔案例真正想表达的内容。盖梯尔案例要表达的内容远不如严格蕴涵句表达的内容那么强。
基于以上两点,严格蕴涵解读方案被公认为是一个失败的解读方案。
(二)反事实条件句解读方案
出于对上文提到的严格蕴涵解读方案面临的第二个诘难,即严格蕴涵解读比盖梯尔案例实际想传递的意思强太多的考虑,威廉姆森(Timothy Williamson)认为对盖梯尔案例的重构应当转向一个较弱的解读方案。威廉姆森主张,盖梯尔案例表达的内容是一个反事实条件句:
前提3:∃x∃pGC(x, p)□→∀x∀p(GC(x, p) →(JTB(x, p)&⇁K(x, p))[19]
前提1仍然不变。所以,根据威廉姆森的解读,盖梯尔案例应被重构为如下论证:
前提1:◇∃x∃pGC(x, p)
前提3:∃x∃pGC(x, p)□→∀x∀p(GC(x, p) →(JTB(x, p)&⇁K(x, p))
结论:◇∃x∃p(JTB(x, p)&⇁K(x, p))[20]
这里有两点需要解释。
第一,如果用自然语言描述,前提3真正表达的意思是:
前提3’:假如某个认知主体x和命题p处于盖梯尔案例的场景中,那么p一定是x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但不是x的知识。
而符号化的前提3并不和自然语言描述的前提3’完全相符。威廉姆森自己也承认这一点[21]。但这并不构成对反事实条件句解读方案的威胁。因为这仅仅是一个形式语义学方面的困难:我们的逻辑工具有限,因而不能对自然语言想表达的意思做到完美刻画。如果我们觉得符号化的前提3有问题,那么我们不妨在脑子里用自然语言将它理解为前提3。这并不影响整个论证的有效性。
第二点需要澄清的是,为何前提3在强度上比前提2更弱。理由如下:公认地,反事实条件句比严格蕴涵句强度弱。我们很容易利用可能世界语义学来解释这一点。对于任意命题p, q,□(p→q)为真要求所有p为真的世界都是q为真的世界;而p□→q为真只要求所有离现实世界最近的p为真的世界都是q为真的世界。所以,利用可能世界语义学来“翻译”,前提2为真要求所有可能世界满足特定要求,而前提3为真只要求某些可能世界——即离现实世界最近的可能世界——满足这个要求。既然前提3比前提2强度弱,那么,攻击前提3就不如攻击前提2那么容易:攻击前提2,我们可以任意对前提2的前件进行细节填充而找到它的反例。但前提3强度更弱,所以我们不容易通过任意对前提3的前件进行细节填充的方式找到它的反例。
那么,在澄清了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反事实条件句解读方案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吗?学界普遍认为,它仍然不令人满意。比如,莫格伦指出,只要稍加设计,我们仍然不难对前提3的前件进行细节填充而找到前提3的反例。比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制造一个实例:现实世界中真的有这样一个“史密斯”,他有理由相信自己容易产生幻觉——以为别人开着福特车上班;而且他有理由相信自己总是记错别人开什么车。那么,在这个实例中,“史密斯”的信念——“办公室里有人拥有福特车”——既没有得到辩护,也不是他的知识。实现这个例子并不难。而这个实例的存在说明,前提3为假:现实世界中确实有认知主体和命题处于盖梯尔案例的场景中,但在现实世界里(也就是离现实世界最近的可能世界里),这个命题不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也不是他的知识)[22]。
简而言之,虽然反事实条件句解读比严格蕴涵解读弱,因而不像严格蕴涵那样容易找到反例,但反事实条件句解读仍然还是太强。稍加设计,我们仍然不难找到前提3的反例。所以,威廉姆森的解读方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严格蕴涵解读方案的困难,但它并不能避免后者遇到的困难:第一,这个重构版本的某个前提,即前提3仍然为假;第二,我们仍然不难找到前提3的反例(虽然比寻找前提2的反例困难一些),说明前提3也不符合盖梯尔案例实际想表达的内容。因此,威廉姆森的反事实解读方案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
沿着威廉姆森的思路,盖蒂斯(Alexander Geddes)对他的方案进行了进一步的弱化。盖蒂斯的弱化方案在于给前提3的后件加上一个限制。他将前提3修改成:
前提3*:假如某个认知主体x和命题p处于盖梯尔案例中,那么通常情况下(normally),p一定是x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但不是x的知识。[23]
这个处理确实削弱了前提3的强度。直觉上,我们认为它更贴合盖梯尔案例要表达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前提3*确实是比前提3更好的解读方案。
然而,盖蒂斯的弱化方案仍然不令人满意。比如,普斯特(Joel Pust)指出,无论对反事实解读方案进行怎样的弱化,这个路径下的解读方案都面临共同的困难:我们对反事实条件句真值的判断往往是经验的,而我们对于思想实验的判断完全是先天的。从这一点来看,反事实条件句也不符合盖梯尔案例要表达的内容[24]。我们以两个反事实条件句为例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假设我们判定“假如张三参加聚会,那么大家一定很开心”为真。我们能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基于我们对张三为人的了解:我们知道他是个逗乐搞笑、讨人喜欢的人。假设我们判定“假如这个坡上没有灌木丛,那么石头会一路滑到湖里”为真。我们能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我们对物理定律有一定的了解。也就是说,我们对反事实条件句真值的判断总是需要经验证据参与。如果缺乏经验证据,我们就难以判断上述两个反事实条件句的真值。但是,思想实验表达出什么内容是基于我们的哲学直觉的。我们对哲学直觉的判断只来自我们对自身的先天反思,是不需要经验信息的。所以,假如盖梯尔思想实验表述的果真是一个反事实条件句,无论是前提3还是前提3*,那么我们在判定它的真值时,势必要借助某些经验信息。那么,我们究竟借助了怎样的经验信息才判定这个反事实条件句为真呢?这个问题似乎非常难回答。事实上,我们就是单纯地凭借先天反思,就认为盖梯尔案例表达的内容令人信服;而那些反对盖梯尔案例的人也是基于纯粹的先天反思认为盖梯尔案例站不住脚。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盖梯尔案例,作出判断的过程都不需要经验参与。笔者认为,普斯特的如上批评是反事实条件句解读方案面临的最大挑战。如果我们能对盖梯尔案例提供一个成功的解读方案,我们必须放弃从反事实条件句出发的路径。
(三)可能性陈述解读方案
不难看出,严格蕴涵解读方案和反事实条件句解读方案都是以“必然性”概念为核心建立的解读方案。如果这两个方案都失败了,那么从必然性入手的路径大概率地都行不通。这也是为何某些学者,如莫格伦,将目光转向了从可能性入手的路径。莫格伦的策略是将盖梯尔案例解读成一个关于可能性的陈述:“可能地,存在处于盖梯尔案例中(如这个案例描述的那样)的认知主体x和命题p, 且p是x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但不是x的知识”[25]。符号化之后,盖梯尔案例被重构为如下论证:
前提4:◇∃x∃p(GC(x, p)&JTB(x, p)&⇁K(x, p))[26]
单凭这一个前提,我们就能得出:
结论:◇∃x∃p(JTB(x, p) ∧⇁K(x, p))
莫格伦解读方案的优点非常明显。可能性命题的强度非常弱,很难找到反例去否定。对于绝大多数可能性命题◇p来说,如果我们认为p没有广义的逻辑矛盾,即不和逻辑规则、语义规则、概念规则等相冲突,我们就倾向于相信◇p为真。显然,我们很难认为莫格伦提出的前提4存在什么逻辑矛盾。所以,由于前提4是一个可能性陈述,这使得它具有了强度很弱因而可信度非常高的优点。
但是,莫格伦的解读方案仍然有两个缺陷。第一个缺陷是普斯特指出的:在莫格伦的解读下,“论证的前提和结论太接近了”[27]。论证的前提里就直接预设了结论。第二个缺陷(实际上也是三种解读方案都存在的缺陷)在于,盖梯尔案例讲述的故事里其实根本没有谈到“知识”概念。莫格伦自己也承认第二个缺陷:“盖梯尔案例的描述表现出中立性——它既没有明确地说认知主体知道命题‘办公室里有人拥有福特车’,也没有明确地说认知主体不知道这个命题。”[28]但是本文讨论的三种传统解读方案都把“知识”概念直接放进对盖梯尔案例的解读中。所以,笔者认为,一个不直接使用“知识”概念的解读方案才更贴合盖梯尔案例本身传递的意思,才是更令人满意的解读方案。
综上所述,三种解读方案各有缺陷。严格蕴涵解读太强以至于很容易被证伪,而且也不贴合盖梯尔案例想要表达的意思。虽然威廉姆森和盖蒂斯的反事实条件句解读在强度问题上作出了改进,但所有反事实条件句解读方案都会面临另一个困难:我们关于反事实条件判断需要经验信息,而我们对思想实验的判断是纯粹先天的,不需要借助经验信息。所以,在这一点上,反事实条件句解读也难以贴合盖梯尔案例想要表达的意思。目前看来,莫格伦的可能性陈述解读方案比前两个解读方案更优。但它仍然存在两个缺陷。接下来,笔者将沿着莫格伦的思路,基于她的解读方案,提供一个改进的解读方案,并解释为何这个方案优于本文介绍的三种解读方案。
三、 盖梯尔案例的逻辑结构:一个改进的解读方案
笔者认为,盖梯尔案例表达的内容并没有直接使用“知识”概念。它真正想传递的意思是:场景中的认知主体的辩护来源是出于认知运气。所以,沿着莫格伦的路径,笔者主张,盖梯尔案例真正表达的内容是:可能地,存在处于盖梯尔场景中的认知主体x和命题p, 且p是x得到辩护的真信念,且这个得到辩护的真信念是出于认知运气得到的。将它符号化,即:
◇∃x∃p(GC(x, p)&JTB(x, p)&EL(x, p))(EL(x, p):p是x由于认知运气得到的。)
笔者认为,这是盖梯尔案例表达的所有内容。那么,我们如何通过这个前提得到最后的结论呢?笔者认为,这是我们在盖梯尔案例讲述的故事之外,另外加了一个前提:认知运气和知识不相容。我们将它符号化:□∀x∀p(K(x, p)→⇁EL(x, p))。但这个前提并不是盖梯尔案例直接传达的,而是我们暗自在心中预设的。所以,笔者认为,盖梯尔案例可以被重构为如下论证:
前提5:□∀x∀p(K(x, p)→⇁EL(x, p))
前提6:◇∃x∃p(GC(x, p)&JTB(x, p)&EL(x, p))
结论:◇∃x∃p(JTB(x, p)&⇁K(x, p))
相较于上文介绍的其他重构方案,这个重构方案有如下四点优势。
第一,保证了前提的可信度。
前提5,即“知识与运气不相容”是知识论领域长期以来的共识[29]。所以,前提5是一个可信度非常高的前提。至于前提6,它和莫格伦的前提4一样,也是可能性陈述。在前文讨论莫格伦的解读方案时,笔者已经论述过,可能性陈述是强度很弱的陈述,不易被反驳。一般来说,对于一个命题◇p, 如果我们认为p没有矛盾,那么我们就倾向于相信◇p为真。所以,前提6继承了前提4可信度高这一优点。总之,在前提的可信度上,本文的重构继承了莫格伦可能性解读方案的优点,避免了严格蕴涵解读方案和反事实条件句解读方案容易遭遇反例的缺陷。
第二,保证了前提的辩护方式是先天的。
前提5和前提6都是通过先天的方式得到的。前提5所说的“知识和运气不相容”是我们纯粹凭借先天的概念分析得到的,它不需要借助任何的经验信息。前提6和莫格伦的前提4都是可能性陈述,对它们的辩护方式是相同的。上文说过,我们对一个可能性命题◇p真值的判断往往是通过考察p是否有广义的逻辑矛盾来进行的:如果我们认为p没有矛盾,那么我们就倾向于相信◇p为真。这样判断真值的方式显然是先天的。所以,对前提5和6的辩护都是通过先天手段进行的,这非常贴合我们对思想实验的理解:思想实验是先天的哲学方法。在这一点上,本文的重构继承了莫格伦可能性解读方案的优点,避免了反事实条件句解读方案的缺陷。
第三,保证了前提没有直接预设结论。
重构后的论证,其结论是从前提5和前提6推出来的。这两个前提都没有直接预设结论。所以,本文的重构避免了莫格伦解读方案的第一个缺陷——其前提直接预设了结论。
第四,符合盖梯尔案例描述的中立性。
在本文的重构中,前提6只表达了关于认知运气的内容,并没有提及任何关于“知识”概念的内容。这种解读更符合我们对盖梯尔思想实验到底讲了什么故事的直觉:它既没有明说认知主体“知道”办公室里有人拥有福特车,也没有明说认知主体不“知道”这一点。因为在认知主体是否“知道”办公室有人有福特车这个问题上,盖梯尔思想实验是沉默的——它根本就没有提及“知识”这个概念(用莫格伦的话来说,盖梯尔案例的描述是“中立的”)。在本文的重构中,“知识”概念是前提5提出来的。而前提5是在盖梯尔案例的描述之外我们独立预设的,并不是盖梯尔案例直接讲述的。也就是说,本文主张,盖梯尔案例讲述的故事仅仅是前提6表达的内容,是我们在阅读盖梯尔案例时自行“脑补”了前提5。这样,本文的重构保证了盖梯尔案例描述的中立性,避免了莫格伦解读方案的第二个缺陷。
总而言之,本文提供的解读方案有两方面的优点:一方面,它继承了莫格伦可能性陈述解读方案的优势,即能够避免严格蕴涵解读方案和反事实条件句解读方案的缺陷;另一方面,它也避免了莫格伦可能性陈述解读方案的两个缺陷。从这两方面看,它是比本文介绍的三种解读方案更优的方案。
四 、结 论
澄清盖梯尔案例的逻辑结构只是一个起点。在此基础上,未来有两方面工作值得尝试。
第一方面的工作是从盖梯尔案例中提取出一个普遍的判断标准:成功的思想实验需要满足怎样的要求,并以这个要求为标准解释“为何某些思想实验更令人信服、某些思想实验争议更大”[30]。笔者主张,一个思想实验如果被认为是成功的,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我们能将它重构成一个有效论证;其二,这个重构符合思想实验想要表达的内容;其三,被重构出来的论证每个前提都能得到辩护。
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重构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我们就倾向于认为这个思想实验是有争议的。比如,公认僵尸案例就比盖梯尔案例的争议大。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在试图将僵尸案例整理成论证时,上面三点要求很难同时被满足。笔者将简要论述这一点。如果我们用“P”指代现实世界所有的微观物理事实,用“Q”指代现实世界的某个心灵事实,比如某人具有疼痛的感受。那么,僵尸思想实验理应被重构成结论是“◇(P∧⇁Q)”的论证。那么,我们是通过怎样的前提得到这个结论的呢?我们真的可以得到这个结论吗?我们可以从僵尸案例描述的故事寻找资源。但是僵尸案例的描述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它只言说了现实世界的某些微观物理事实,但并没有言说现实世界的所有微观物理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即便我们一条条地列举现实世界的微观物理事实,我们也只能列举我们已经掌握的事实,但这并不是所有事实:未来的科学发现总会告诉我们更多物理事实[31]。所以,我们能够得到的结论只能是◇(S1∧S2∧…Sn∧⇁Q,其中Sn是关于现实世界的某一条微观物理事实),但这个结论和僵尸案例想要得到的目标结论“◇(P∧⇁Q)”存在差距(gap)。简而言之,在澄清僵尸案例逻辑结构的过程中,我们会面临困难:我们甚至不知道怎样将这个案例重构成一个有效的论证。而在重构盖梯尔案例的逻辑结构时,我们可以做到本文总结的三个要求。所以,这个区别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某些思想实验更令人信服,而某些思想实验争议更大。当然,仅仅通过对两个思想实验进行重构,很难证明笔者主张的理由是充分的。我们需要通过对更多的思想实验进行重构来验证这一点。
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希望以澄清思想实验的逻辑结构为起点,来抵制实验哲学对“扶手椅”哲学工具的攻击。诚然,如实验哲学家的调查结果所示,我们对思想实验的判断并不是稳定的,但这很有可能是我们受到了思想实验表面语言的干扰,而不是因为思想实验这个工具本身靠不住。为了证明这个猜想,我们可以进行更多的问卷调查。比如,我们可以让被试阅读用自然语言描述的思想实验和让被试阅读用逻辑语言描述的思想实验,并比较调查结果。如果调查结果显示,被试在阅读用逻辑语言描述的思想实验之后能输出稳定的判断结果,那似乎就能说明人们对思想实验判断的不稳定性来自于语言的干扰,而非因为思想实验本身是不可靠的工具。当然,这只是对未来的猜测,具体结果怎样还需要调查数据来验证。
以上两点是对未来工作的展望,并不是已经得到验证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从澄清思想实验的逻辑结构入手,解释思想实验争议的根源,以之来抵制实验哲学对传统“扶手椅”哲学的攻击,是一个值得尝试的工作方向。
【注释】
[1]Edmund L.Gettier,“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 Analysis 23,no.6 (June 1963):121-123.
[2]David J.Chalmers,The Conscious Mind:In Search of a Fundamental Theor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95-96.
[3]John R.Searle,“Is the Brain’s Mind a Computer Program?” Scientific American 262,no.1 (January 1990):26-31.
[4]Judith Jarvis Thomson,“Killing,Letting Die,and the Trolley Problem,” The Monist 59,no.2 (April 1976):204-217.
[5]Hilary Putnam,“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Language,Mind and Knowledge,ed.Keith Gunderson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5),131-193.
[6]查莫斯(David Chalmers)汇总了大多数批评,参见:David J.Chalmers,“The Two-Dimensional Argument Against Materialism,” in The Character of Consciousnes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154-184。
[7]Edouard Machery,Philosophy Within Its Proper Bound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6-8.
[8]类似的工作在语言哲学领域已非常常见。比如,罗素就试图澄清语言的逻辑结构以消除自然语言由表面的语法结构造成的困扰。
[9]Anna-Sara Malmgren,“Rationalism and the Content of Intuitive Judgements,” Mind 120,no.478 (April 2011):264.
[10]“尽量”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排除这个思想实验本身就有错的情况。如果无论怎样重构,我们都不能把一个思想实验整理成一个可靠论证的形式,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这个思想实验本身就有问题。
[11]Joel Pust,“Intuiti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9 Edition),updated May 6,2019,accessed March 4,2022,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9/entries/intuition/.
[12]Joel Pust,“Intuiti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9 Edition),updated May 6,2019,accessed March 4,2022,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9/entries/intuition/.
[13]Joel Pust,“Intuiti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9 Edition),updated May 6,2019,accessed March 4,2022,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9/entries/intuition/.
[14]Joel Pust,“Intuiti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9 Edition),updated May 6,2019,accessed March 4,2022,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9/entries/intuition/.
[15]参见:Timothy Williamson,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 (Oxford:Blackwell,2007),185;Anna-Sara Malmgren,“Rationalism and the Content of Intuitive Judgements,” Mind 120,no.478 (April 2011):274-275;Alexander Geddes,“Judgements about Thought Experiments,” Mind 127,no.505 (January 2018):38;Pierre Saint-Germier,“Getting Gettier Straight:Thought Experiments,Deviant Realizations and Default Interpretations,” Synthese 198,no.2 (February 2021):1785-1786。
[16]Pierre Saint-Germier,“Getting Gettier Straight:Thought Experiments,Deviant Realizations and Default Interpretations,” Synthese 198,no.2 (February 2021):1785.
[17]Anna-Sara Malmgren,“Rationalism and the Content of Intuitive Judgements,” Mind 120,no.478 (April 2011):275.
[18]Anna-Sara Malmgren,“Rationalism and the Content of Intuitive Judgements,” Mind 120,no.478 (April 2011):276。
[19]Timothy Williamson,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186.
[20]Timothy Williamson,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186-187.
[21]这里涉及所谓的“驴子回指(donkey anaphora)”问题。参见:Timothy Williamson,The Philosophy of Philosophy,195-199。
[22]Anna-Sara Malmgren,“Rationalism and the Content of Intuitive Judgements,”Mind 120,no.478 (April 2011):279.
[23]Alexander Geddes,“Judgements about Thought Experiments,” Mind 127,no.505 (January 2018):48.在盖蒂斯的文章里,他没有给出前提3*的符号化表达。普斯特(Joel Pust)也指出这一点。但这不构成理论困难:并不是所有自然语言都有必要进行符号化表达。即便没有符号化,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前提3*表达的意思比前提3更弱。参见:Joel Pust,“Intuiti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9 Edition),updated May 6,2019,accessed March 4,2022,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9/entries/intuition/。
[24]Joel Pust,“Intuiti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9 Edition),updated May 6,2019,accessed March 4,2022,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9/entries/intuition/.
[25]Anna-Sara Malmgren,“Rationalism and the Content of Intuitive Judgements,” Mind 120,no.478 (April 2011):281.
[26]Anna-Sara Malmgren,“Rationalism and the Content of Intuitive Judgements,” Mind 120,no.478 (April 2011):281.
[27]Joel Pust,“Intuition,”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19 Edition),updated May 6,2019,accessed March 4,2022,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19/entries/intuition/.
[28]Anna-Sara Malmgren,“Rationalism and the Content of Intuitive Judgements,” Mind 120,no.478 (April 2011):274.
[29]关于“知识与运气不相容”的观点,参见:Duncan Pritchard,“Virtue Epistemology and Epistemic Luck,” Metaphilosophy 34,no.1/2 (January 2003):106-130;Wayne Riggs,“Why Epistemologists Are so down on Their Luck,” Synthese 158,no.3 (October,2007):329-344。
[30]当然,如果我们对更多的思想实验进行重构,我们的总结或许更加可靠和完善。
[31]这也是为何僵尸论证会遇到所谓的“C类”物理主义者的抵制。在“C类”物理主义者看来,未来一旦我们获取了更多的科学知识,我们就不会相信僵尸案例。“C类”物理主义是查莫斯的命名。关于他对物理主义的分类,以及各类物理主义的立场,参见:David J.Chalmers,“Consciousness and Its Place in Nature,” in Philosophy of Mind: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258-260。
